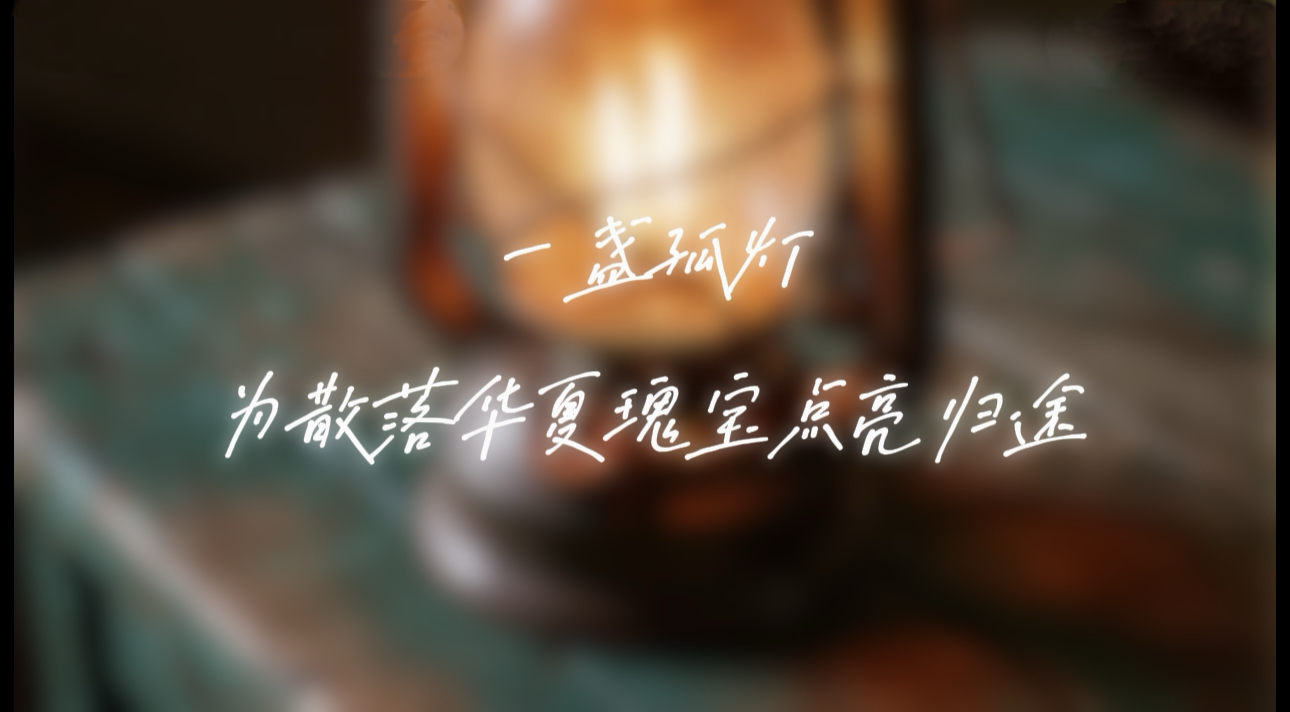編者的話
夏天,像一封藍(lán)色的信,信封上寫著“海”的名字。有些人把腳印留在海灘,有些人把心事埋進(jìn)浪里,還有些話,只說給海聽。年年夏日,海都在那里——不變的是浪花拍岸,變的是你我與它之間,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情緒。那些你以為已經(jīng)風(fēng)干的片段,海,一直都記得。
歡迎把你的作品發(fā)給“五月”(v_zhou@sina.com),與“五月”一起成長。掃碼可閱讀《中國青年作家報(bào)》電子版、中國青年報(bào)客戶端、中國青年作家網(wǎng),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學(xué)花海。

---------------
海上列車(小說)
高星雨(26歲) 安徽省蚌埠市龍子湖實(shí)驗(yàn)學(xué)校教師
不知道多少次了,余萱乘著海上列車往返于島內(nèi)和島外,出神地望著窗外的夕陽。大片金黃的、火紅的、煙紫的光芒鋪灑在海面上,然后一縷一縷被海水吸收。列車在海面上向前行駛,海水不斷后退,影子在波光涌動(dòng)之間格外鮮活。這是余萱一天里最緩慢的一刻,等她按時(shí)到達(dá)島外的站點(diǎn),夕陽懸于海平面之上,恰好是圓和線相切的場景。
余萱出了地鐵站,熟練地找到自己的電動(dòng)車,騎車前往母親的小飯館。母女倆忙忙碌碌,晚上8點(diǎn)左右,余萱的父親也會(huì)到店里幫忙。9點(diǎn)多的時(shí)候,他們一家三口乘著閩南溫潤的晚風(fēng),說說笑笑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余萱一家不是閩南人,10歲時(shí)她跟隨父母從安徽搬遷到這里。母親開起了小飯館,賣淮南牛肉湯。她隨父母遠(yuǎn)遷至此,無論是氣候還是飲食都有不小的差異。時(shí)間久了余萱也能講閩南話,但一家人關(guān)起門來,還是會(huì)說江淮官話。曾經(jīng),方言的切換讓余萱在身份認(rèn)同的問題上反復(fù)橫跳。如今,島內(nèi)島外的生活也讓余萱感到割裂。海上列車連接著島內(nèi)和島外,列車往返時(shí),她的身份也隨之切換。在島內(nèi),她是數(shù)學(xué)老師,承受著不小的工作壓力。在島外,她是小飯館的服務(wù)員,盡情地?fù)肀е碎g煙火。
傍晚時(shí)分,海上列車駛過海面,她讀過的那一句“半江瑟瑟半江紅”在腦海里時(shí)隱時(shí)現(xiàn)。她透過車窗望著無邊的海域,一整天的疲憊漸漸拋諸腦后。仿佛這一程不是歸家,而是精神的逃逸之旅。漸漸地,各種不快都在這趟列車上消解,如石子投入深海。取而代之的是母親的呼喚、父親的笑聲、顧客的吆喝和路人的從容。
每當(dāng)系上圍裙,面對(duì)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,余萱就成了電影中的客串演員。小飯館每天都在演奏一場奇妙的交響樂,人們品嘗著外鄉(xiāng)的美食,沒有人特別在意余萱的舉動(dòng)。哪怕有一天她沒有到店里幫忙,也不會(huì)有人提起她。更多時(shí)候,顧客招呼她過來時(shí)連頭都不抬,眼睛只盯著手里的菜單。在這里,沒有人知道她是老師。生意不多的時(shí)候,她也會(huì)和熟悉的客人嘮上幾句。微咸的海風(fēng)吹過,有時(shí)還帶著鳳凰花的花瓣,柔柔地落到余萱的肩頭。她習(xí)以為常地?fù)廴セò辏χ阗~,主動(dòng)提出抹零,偶爾還會(huì)提醒顧客帶好隨身物品。
內(nèi)陸人多喜歡大海,余萱也不例外。這天飯館打烊之后,她和母親在海邊散步。浪花一波一波地?fù)湎蛏碁:吞於寄Y(jié)著幽深的藍(lán),世界仿佛是一個(gè)巨大的玻璃瓶,瑩潤透光。余萱脫下洞洞鞋,赤腳踩在沙灘上。她望著架在海面上的軌道,想到自己早晨乘車去往島內(nèi)的經(jīng)歷。朝陽升起時(shí),陽光斜照著車廂,穿過玻璃仍然十分刺眼。每一個(gè)工作日的早晨,列車?yán)锏挠噍鏁?huì)感到眩暈,迷離,灼熱——大海遼闊,卻無法容納工作帶來的壓力和焦慮。
母親輕聲問:“萱萱,你是不是太累了?”
她笑著道:“沒有,只是有些恍惚。讀了這么多年的書,如今好像不太教得明白。”
“我早就說啦,讓你下班就回家休息,不要到店里來。”母親說。
她沒有回應(yīng),隔著朦朧的月色,她看不清母親的臉。海風(fēng)從背后吹來,余萱幽微的嘆息聲被浪花吞沒。遠(yuǎn)望天際,那朵云棲息在海面上,不知明天會(huì)在何處灑下雨點(diǎn)。
母女倆沿著海岸線往前走,快到家的時(shí)候,母親突然說:“萱萱,如果你工作得不開心,是可以辭職的。”
“媽,我沒有……”余萱回過頭去望著母親,那些準(zhǔn)備用于狡辯的話終究沒有說出口。
那一刻,母親的眼睛里星河暗涌,匯聚成世界上最小的海。
---------------
咸印記
譚鑫
海是咸的,這種常識(shí)在我20歲以前,從未真正屬于我。
老家存鹽慣用的陶罐,倒是我熟悉的物件。那些白花花的晶體,每次自罐口出落,如同我幼時(shí)想象里海灘的細(xì)沙一般,靜靜流瀉而下。鹽粒在陽光里剔透晶瑩,似乎也映照著遙遠(yuǎn)的、未曾謀面的海水,又如同無數(shù)微小棱角,在罐子深處默默蓄養(yǎng)著海的神韻。
外婆做菜時(shí),總喜歡將細(xì)鹽先舀進(jìn)勺子,再撒入鍋中,無論是舀還是撒,都會(huì)嗞嗞作響,那聲音仿佛海風(fēng)在輕輕呼吸,又似遠(yuǎn)處浪濤的隱約召喚。我站在旁邊,每每看著鍋邊縷縷輕煙飄散,仿佛那煙塵里也裹著來自遙遠(yuǎn)大海的氣息,它飛越千山萬壑,最終輕輕彌散于我們這方小小廚房中。
幼時(shí)父親在外做工,每次他風(fēng)塵仆仆地回家,身上總會(huì)攜著汗水的氣味,熱烈而真切,有時(shí)即便沒見到人,但在屋中一聞到那種咸味,我就知道鐵定是他回來了。
父親有件褪色的迷彩服,總被他當(dāng)做工裝穿,因此浸透了無數(shù)日夜的汗水,后背處也變得發(fā)白。縱然每次回來,衣服都會(huì)被母親洗干凈,恢復(fù)本色,近聞也只剩清爽的肥皂味。但只要一晾院中,便如一面無聲招展的旗,我一看到,便會(huì)感覺有海風(fēng)般的咸味氣息彌漫在整座小院,像一種視覺上的刻板記憶。
現(xiàn)在看來,那一片我彼時(shí)未曾謀面的大海,以這般具體而細(xì)微的咸澀滋味,早已滲透進(jìn)我的生活日常。
高中的地理老師也教過我堂哥,他的課我總是正襟危坐。地理課本上畫著海,那些由藍(lán)色顏料涂就的平面,彎彎曲曲的等高線如睡蛇伏在紙上,勾勒出海岸線的輪廓。里面的藍(lán)色深得如同幽遠(yuǎn)的夢境,我手指曾無數(shù)次輕輕拂過那些紙上的海,撫過那些靜止的等高線,也曾在課間小憩時(shí),側(cè)耳傾聽般枕著它入眠,卻終究無法從這紙頁上,聽出半點(diǎn)兒濤聲。
對(duì)于從小生活在內(nèi)陸城市且18歲前都沒出過小城的我來說,那些藍(lán)色紙頁上的海,終究只是一些平面符號(hào),一個(gè)遙遠(yuǎn)而無法觸及的象征,既無生命,也無呼吸,更無那傳言里能吞沒一切的磅礴力量。
自然,海在我心里,也漸漸囤積成了一片懸在生活邊緣的巨大謎團(tuán)。它既在鹽粒里呼吸,又于汗水中蒸騰;更是課本上凝固的圖畫,還仿佛真實(shí)地存在著,卻在我的生活中始終存在,像隔著一層無法穿透的厚厚的簾,從未真正屬于我。
一個(gè)夏天,我在深圳參加某個(gè)比賽,活動(dòng)中有一個(gè)下午的間隙,我臨時(shí)起意決定去看海,哪怕它并不足夠遼闊。
車輪飛轉(zhuǎn),窗外風(fēng)景急速向后飛逝,我坐在顛簸的車?yán)铮中睦锞刮⑽B出了汗,不知是否因?yàn)樾闹写е嚓P(guān)于海的咸澀想象,這汗意也咸?心中反復(fù)跳動(dòng)著關(guān)于海的種種猜測:那海的藍(lán),究竟會(huì)藍(lán)到何等程度?海的聲響,又該是如何響徹云霄?所有想象中海的宏大,仿佛正悄悄壓上我的胸口,讓我既興奮又有些莫名的惶然。
我終于站在了海邊,眼前的地平線豁然開朗,幾乎令人眩暈。視線盡頭那無垠的蔚藍(lán),竟如此直截了當(dāng)?shù)胤指盍颂斓亍>薮蟮乃{(lán)色似乎隨時(shí)要傾覆而下,將我吞沒其中。海風(fēng)撲面而來,帶著強(qiáng)勁的、不容置疑的力量,也裹挾著濃烈的咸腥氣味,仿佛無數(shù)生命在涌動(dòng)呼吸。
我走向浪花奔涌的岸邊,海水帶著沁涼之意漫過腳背,又迅速退去,如同巨大生命體溫柔地觸碰與呼吸。我莫名地蹲下身,用手指蘸了一小抹海水,情不自禁地輕輕送入口中——剎那間,那股熟悉的、濃烈的咸味在舌尖彌漫開來,像對(duì)我此前接觸到那些“海”的記憶的回收。
那天,我沒有像一個(gè)初遇大海的人那樣興奮,就連拍照都很少,只一個(gè)人默默地走在海邊,從午時(shí)待到日落。倒不是故作鎮(zhèn)定,更像一種覬覦已久的渴望終于延遲滿足的心安,偶爾閉眼呼吸,側(cè)耳傾聽,聞著熟悉且真實(shí)的咸咸海風(fēng),突然感覺那些地理課本上靜止的圖案,此刻竟也活了起來,原來海不只是平面的圖景,而是無數(shù)生動(dòng)的等高線在日夜奔騰。
自此之后,每每見到家中那個(gè)鹽罐,我總會(huì)想起那天海水推著浪花涌上腳背的沁涼;而父親即將到了退休年紀(jì),他的身上很少再有那些熟悉的汗味,我反而成了家中汗流得最多的那個(gè)人,想來理應(yīng)如此,就像海浪不只是轟響不息,也有守護(hù)和傳承的前赴后繼。
人心中常常揣著關(guān)于遠(yuǎn)方的謎題,海也是希望的象征之一,其實(shí)答案未必在遠(yuǎn)方尋覓。正所謂“謎底就在謎面上”,那天立于海天之間,浪花退去,腳底沙礫顯露的瞬間,我才后知后覺:那浩渺之海,并非遠(yuǎn)方之物,也從未曾真正離開過我們,它只是以一種更細(xì)微、更堅(jiān)韌的方式,融入我們呼吸的空氣,滲入我們勞作的汗水,棲息于我們生活的核心深處,匯入奔波流動(dòng)且每天相伴的尋常之中。
只是,被生活的瑣碎浮云遮望眼的我們,偶爾也需要親自來到它面前,宛如朝圣般,鄭重地認(rèn)領(lǐng)這份本屬于我們生命背景的咸澀與遼闊。
---------------
遙遙看海(小說)
馮嘉美(24歲)
10歲以前,我都住在城市的鋼筋叢林里,了解自然的途徑主要靠色彩斑斕的顯示屏。我時(shí)常幻想寬闊無垠的草原或是綿延起伏的高山會(huì)是我素未謀面的家鄉(xiāng)。直到某個(gè)暑假,我隨父母乘坐老式客船去一座海島,我得以見到一片望不盡的海。
我不太喜歡海,聞見父母身上的咸腥海風(fēng),總覺得鹽晶顆粒從骨頭里長了出來。還有那摸不清楚的海潮,即便緊緊跑在父親身后,浪也總是能打在腳踝上,生疼。
所以我坐在遠(yuǎn)處的石頭上,遙遙看海。
我一人看海,有人看到了我。他是彭家的孩子,大家都叫他小海。他比我大3歲,性格開朗像有無盡活力。小海哥把我拉進(jìn)小團(tuán)體中,我們奔跑過小島的每寸土地,越跑越快,化作了風(fēng)穿過大廣場,穿過百年宗祠。
我止步在大海前。
“嘉!過來!”小海哥高聲喊著。他身后的人也隨之呼喊起來,耳邊哪里還聽得到海風(fēng)呼呼。少男少女的誠摯燒干了冰冷,我終于大膽起來,走向那片海。
天下起雨,孩童的驚呼聲與雷聲相伴,欲與天爭一個(gè)氣勢高低。我們拉住彼此跑回家,路上我把膝蓋磕得血肉模糊,但挨父母的責(zé)罵時(shí)卻感覺不到任何的疼痛。在那個(gè)下午,聽不太明白的鄉(xiāng)音喚著我,教我識(shí)別貝殼,教我讀懂潮汐規(guī)律,我突然認(rèn)識(shí)了大海,然后同它和好,轉(zhuǎn)頭看稚嫩柔善的臉龐在身側(cè),有什么比這些更解不開偏見的。
自那次后我常去找小海哥他們玩,可父母嘮叨說玩樂不是長久之事,不如抓緊時(shí)間看看書、努努力。我不能順從他們的話,此刻的玩樂不是命運(yùn)對(duì)我這個(gè)年紀(jì)的寬宏允許嗎?父母不這樣認(rèn)為,他們說小海哥他們出不了島,是沒出息的人。
我很生氣,出息由什么定義?是向上尋求的代代期望,還是向下對(duì)未知前方的憂慮?
我再次去找小海哥玩,還沒到門口,卻見他慌忙闖出。朱家的小弟和家里鬧矛盾找不見了人影,伙伴們滿島尋找,終于在一處巖石的縫隙處發(fā)現(xiàn)他。小海哥最為聰明冷靜,他一邊安排人叫大人,一邊讓大家把衣服脫下給他保暖。待把人拉上來的時(shí)候,又發(fā)現(xiàn)小弟腳踝受了傷,小海哥好像生來什么都知道,他固定并包扎傷口再背起人朝最快回家的小路上走去。
陰冷的雨里,我們追逐著他如同追著唯一的火光。這樣的人怎么會(huì)沒有出息?
小海哥成績優(yōu)異,我有許多解不開的題目他都能幫忙作答。可惜礙于各種條件,他去了離島最近的普通中學(xué)。以前,我會(huì)帶一種無緣由的憐憫去看他們這些島上的孩子——海的無界似有界,將他們攔在此處。可見過小海哥后,如同靠近大海般,咸腥的味道不再長成鹽晶,海的波浪也可以把他們搖去遠(yuǎn)方。
離開島的頭天晚上,我和小海哥他們坐在大廣場上聽外來的戲班子唱戲。臺(tái)上唱著,臺(tái)下的親朋揶揄我,說城市叢林有什么好,我或許仍然是寂寂無名的“草食者”。我才發(fā)覺陸上的偏見,海這頭同有。
小海哥插話替我解圍,又用合理的借口拉上我跑走了。大海邊我們再次玩起找貝殼的游戲,我們找到相似的貝殼,但仔細(xì)看來,自然賜予的紋路又是絕世無雙。我明白他是借這游戲安慰我,不過我更驚訝于他處事的成熟遠(yuǎn)超同輩。我愈發(fā)覺得,他是父母口中有出息的人。他說以后想當(dāng)醫(yī)生,“做醫(yī)治病還得功德”。
回到城里后,很長一段時(shí)間我像頭水怪堪堪變作人形難適應(yīng)陸上的種種,我時(shí)常想那座小島,那片無邊海,和名字里帶海字的人。
長大后為了打破當(dāng)年戲臺(tái)下的嘲諷,我拼命朝叢林外闖去。只是,我時(shí)常想那片海。
我回了家鄉(xiāng),得知小海哥高中時(shí)和家人出海,遇上風(fēng)暴,用一條腿換回生命,在島上開了一家診所。我找過去,停在不遠(yuǎn)處看用黑色毛筆寫的招牌,招牌下還有一串字介紹涼茶。我正專注看著,一個(gè)拄著拐杖的年輕人走出來。他身板挺拔,手里提著水壺,要倒水給前來的病人。我怎么看他,怎么是意氣風(fēng)發(fā)。
我沒有上前,莫名想起那段戲詞,“舊地重游,只剩得梅魂月影,依稀似夢,夢里故人無蹤”。此情此景,我不知道要不要用人事全非形容,我替他惋惜,兒時(shí)志向像是被拆碎又勉強(qiáng)圓滿,可忽然,我驚覺自己再次患上了曾經(jīng)的病——憐憫的偏見。外人的評(píng)判不能替他做主,我也不能。
我最后沒有和小海哥打招呼,而是再次繞去海邊。經(jīng)年流去,心態(tài)早已翻天覆地,我僅是平和地,淡然地,遙遙看海。
---------------
在日照等待一場名叫青春的日出
家民
在日照的第一晚睡得特別香,整夜無夢。我醒得很早,穿過碧海路的時(shí)候,彎彎的月兒還高高掛在天上。
日照因“日出初光先照”而得名,日照的海,據(jù)說是東方的第一縷晨光落下的地方。而我,今天趕赴的就是一場日出,一場黃海的日出。沙灘上已經(jīng)聚集了不少人,最讓我意外的是,人群中大多是年輕人,躺平、喪、宅,似乎通通與他們無關(guān)。人們面朝東方等待著,眼中都閃著一種微光——那是對(duì)日出的期待,對(duì)希望的渴求,是對(duì)某種不確定的美的信仰。舉著手機(jī)直播的阿姨,鏡頭對(duì)準(zhǔn)日出的方向,替不能來到現(xiàn)場的觀眾等候晨光;把三腳架立在沙灘上的女孩,將自己作為前景嵌入海天,擺出各種姿勢;一位年輕的母親,用浴巾抱著熟睡的孩子,裙擺被海風(fēng)輕輕揚(yáng)起;一位耄耋老人,靜靜地坐在藤椅上,面朝大海,眼睛微閉,不說話,不拍照,也不催促,只有頭上不多的白發(fā)在飄蕩;一個(gè)男孩赤裸著上身,站在插滿玫瑰花的沙灘上,身旁是幾個(gè)空啤酒瓶——那是青春的符號(hào),也像是某種宣言。
一陣熟悉的音樂傳來,是《最炫民族風(fēng)》。旋律流轉(zhuǎn)間,這片晨色里的生活氣息,愈發(fā)真實(shí)起來。誰說青春必須是沉默的詩?它也可以是張揚(yáng)的、熱烈的,哪怕是在等待將現(xiàn)的光里。
盡管頭頂是蔚藍(lán)色的天空,但云卻仍然簇?fù)碓跂|方的遠(yuǎn)處——顯然,太陽會(huì)如期而至,但海上日出肯定要失約了。身邊有女孩在模擬著用手托起那輪看不見的太陽,忽然令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的海上日出。30多年前在北戴河,也是這樣一個(gè)清晨,爸爸媽媽帶著我和妹妹坐了20多個(gè)小時(shí)的火車去看海,去看海上日出。那次也是云涌東方,但幸運(yùn)的是在日出那一剎那,云似乎被太陽推開了,才讓我和妹妹的手中能夠托起了剛剛升起的紅日,被相機(jī)定格為永恒。時(shí)至今日,照片已然泛黃,但那日出已經(jīng)嵌入眼眸、刻在心底。今天的日照海灘,雖然沒有了海上日出,但有著同樣熾熱的目光。
在大海的眼里,它會(huì)怎么看這些早起看日出的人呢?在它眼里,或許每個(gè)人都是一樣的,正如在我們眼里,每朵浪花都是一樣的。但對(duì)我們每個(gè)人來說,這個(gè)清晨,這片海灘,這些遇見的人和事,都是獨(dú)一無二的。人生如海,潮起潮落中,沒有人能預(yù)知下一次日出是否如期而至。就像去年,媽媽突發(fā)重病,一家人在急診室門前一圈又一圈徘徊,心如懸旌。那時(shí)我第一次意識(shí)到,日出并非理所當(dāng)然——今天的你還能看見,明天也許還能看見,但后天呢?誰都不能確定。
我隨手撿起一枚平平無奇的貝殼,甚至邊緣有些缺損,打算把它帶回家,把它和那張照片放在一起。因?yàn)樗鼘儆谖?mdash;—屬于這片海,屬于這個(gè)早晨,也屬于那份無果卻依然堅(jiān)定的等待。日照曾是古代齊魯商船南下的重要港口,是漢唐時(shí)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的北起點(diǎn)之一。它日日等待著風(fēng)帆的到來,凝望大海深處遠(yuǎn)行的背影。有人說:“莒,是齊魯東望的眼睛。”2000多年前的莒人,在齊魯之間建國立制,出兵伐齊,鑄劍鑄鼎。他們應(yīng)該也曾站在這片海邊,遠(yuǎn)眺著黃海之東的未知吧?今日我所在的海邊,或許就是那看向世界的地方——朝東,望海,等光。
還有那浮來山的“天下銀杏第一樹”。它也在這片土地上站立了3000余年,如今依舊枝繁葉茂。有人說,它曾見過孔子的足跡;也有人說,它知曉齊魯悲歌的節(jié)拍。但我更喜歡銀杏樹邊那座極富童趣的小殿——三爺?shù)睿〉街蝗輧扇送瑫r(shí)在里面。三爺?shù)罟┓钪?ldquo;筋骨爺爺”“咳嗽爺爺”“疙瘩爺爺”,他們個(gè)個(gè)都像從村里迎面走來的老爺爺,慈眉善目,等著為你解除病痛。
回賓館的路上,我找到了音樂的來源:一群早起的阿姨在跳廣場舞,紅扇翻飛,面朝大海。她們跳得認(rèn)真,不為觀眾,只為自己,每個(gè)人臉上都洋溢著青春的光彩。歷史很遠(yuǎn),生活很近,而青春,就在這兩者的夾縫里,燦然盛放。青春,不總是轟轟烈烈。更多時(shí)候,它像銀杏樹一樣無聲成長,像三爺?shù)畹南慊鹨粯訙厝岢掷m(xù),像清晨的沙灘上一雙雙眼睛那樣,不知結(jié)果地等待。青春是一場關(guān)于“等待”的修行——不是每個(gè)愿望都能實(shí)現(xiàn),但每一次等待,都是一場抵達(dá)。
也許,真正的日出,未必在東方,而是在每一個(gè)愿意早起、敢于等待、勇于相信的人心里——因?yàn)榍啻海辉谌粘瞿且豢蹋诔蜿柟獾哪莻€(gè)姿勢里。
---------------
時(shí)光慢走,我的小島
王磊斌
在舟橋3號(hào)輪的舷欄上,被犁開的白色浪條一路后撤,眼前就只有這純粹的藍(lán),激爽的浪。我緊緊拉握住船欄,將身子向前傾去,暢享海風(fēng)入懷的自由。哪顆心不慕海呢!身旁的孩童騎在父親的肩上,張開雙手,興奮地叫喊著,化作海鷗翱翔,我望向不遠(yuǎn)處那橫亙于兩島之間的大橋,定格下了“歸途”中的一瞬美好。
這一次回島,時(shí)間是極空裕的,故而有了更多興致,選擇走走停停看看。
會(huì)因突然一日的早醒,選擇在凌晨4點(diǎn),獨(dú)自在家的庭院里守候日出。看著金青大橋從灰暗漸變?yōu)樯钏{(lán),然后慢慢披上金燦,直到紅日一躍的一剎那,橋與海融化在朝陽的絢爛里。
會(huì)在中大街吃完一碗久違的青沙餛飩后,特意走進(jìn)新改造的漁俗館內(nèi),看看外公外婆年輕時(shí)住過的地方,駐足觀望一池的夏荷,抹去老灶臺(tái)上的一層落灰,然后被一拎攤開的漁網(wǎng)上掛著的幾處漁結(jié)繩,觸發(fā)一席的回憶。
會(huì)在午后三四點(diǎn),去一處熱鬧的沙灘,基湖的、五龍的、高場灣的……在蒼穹之下,是一目望不盡的碧海金沙。赤腳踩在松軟的沙上,迎著浪潮跳躍著,一個(gè)猛子扎進(jìn)咸咸的海里,除去歲月的塵垢,重回那個(gè)愛淘氣撲水的少年。
會(huì)在稍涼快些的傍晚,登上島的最高處——大悲山,在清凈的佛門前,伴著東海呢喃,靜待夕陽西下,云蒸霞蔚。有時(shí)也會(huì)騎車至離家不遠(yuǎn)處所新建的“千帆臺(tái)”,臨臺(tái)觀滄海空闊,夕照千里,生蕩出“天地悠悠”的感慨。
會(huì)在飯過小憩后,隨著島上的老老少少慢走,經(jīng)過精致凈爽的微城,穿出以彩繪藍(lán)天作頂?shù)男〔藞@隧道,沿坡向上,左岸是一望無垠的海,直到遇見十里金灘特色小鎮(zhèn)——這里有喧囂火爆的排檔夜市,有藍(lán)調(diào)抒情的室外酒吧,還有發(fā)光看臺(tái)的長椅上納涼的情侶們。還想繼續(xù)走的時(shí)候便隨性地去聞聞基湖與高場灣交界處那片黑松林的味道,去尋一片初來乍到的向日葵花海,看它們的花盤在星河月光下隨著海風(fēng)搖曳。一路上,繪在墻上的漁民畫趕去無聊,漁家人日常間樸素的景,讓人心安有了停泊處。
會(huì)時(shí)不時(shí)將過去30年里在島上的記憶碎片,在腦海里剪輯成散亂沒有邏輯的短片,在島上的景、在島上的人、在島上的事,甚至于一抹在島上的獨(dú)特感受,都試著在與故人的閑聊間、在過去泛黃的日記本上、在聚餐中一次次喊著不易的碰杯里,用力歸攏,拼貼,然后回味。
許多人都笑我是閑置下來的身子里包裹著一顆庸碌的心,我總是應(yīng)以一笑。因?yàn)槲宜鶒鄣男u,它也是這樣的脾性,享受著一種習(xí)慣性的孤獨(dú),遠(yuǎn)離塵囂與繁瑣,閑散地臥躺在東海里,但卻時(shí)不時(shí)關(guān)心下海風(fēng)與云霧,時(shí)不時(shí)嘮叨下潮鳴與月涌,時(shí)不時(shí)用燈塔閃射的光提醒黑寂的海不要睡去。
哎,時(shí)光就慢些走吧,我的小島。
- 2025-07-14新書速遞丨如何富有智慧地與青春期的孩子相處
- 2025-07-11在書店的渡口,不趕路只悠游
- 2025-07-11讓閱讀成為最潮的消暑方式
- 2025-07-11總被自己的“小怪癖”逼瘋?這本暢銷書,藏著讀懂自己的密碼

 西北角
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(wǎng)微信
中國甘肅網(wǎng)微信 微博甘肅
微博甘肅 學(xué)習(xí)強(qiáng)國
學(xué)習(xí)強(qiáng)國 今日頭條號(hào)
今日頭條號(hào)